周六荐书|民初教科书的多重面相
撰文:瞿骏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清末民初的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转型时代,关注民族,国家和自身命运的读书人为因应西潮掀起了种种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在《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0月)中,作者通过对学生生活、教科书、“排满”革命等问题的细腻考察,重塑清末民初读书人的群体形象,尝试挖掘这些读书人当时生活、行动与心境的几个侧面,解说清末民初中国的变之深与变之痛。
以下内容受权选摘内容摘自该书第六章第二节。
在考察了教科书的出版与民初新教育结构的互动影响之后,民初教科书编写理念和其内容的多重面相亦值得我们多加注意。通读《共和国教科书》我们会发现其编写理念基本上植根于富强与进化观念,着力于所谓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这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就已出现的变化,到清末则成为几乎每个读书人都受其影响的时代风气,民初则仍在延续。正如刘延陵所说,“辛亥以前中国屡蒙国耻,举国上下最热衷于富国强兵,报仇雪耻”。
《共和国教科书》谈到上海会立即引申至租界与国耻的粘连,说:“我国所谓租界,其管理地方之权,概归外人,不独上海一地为然,此国之耻也。国民宜善谋其国,使我政教昌明,国势日盛,乃可以雪耻耳。”谈到唐太宗则希望能“隐寓尚武强国之道”;教《木兰诗》要学生领会“女子亦有军国民资格”;讲铁路则夸其“便行旅,便输运,平时已获益匪浅。军兴时朝发夕至,成败利钝,悉系于此”,“为工战、商战之利器,更为兵战之利器”。
上述课文所宣扬的理念在时人看来因为世界潮流日新月异,瓜分危机日急夜迫,列强又经常以强权代替公理,所以其非但具备合理性,且要强调其紧迫性。不过《共和国教科书》虽有大量篇幅宣扬国家富强和社会进化,却并不仅有这一个面相,其另外两个隐而不彰的面相更值得我们加以讨论。首先即是民初教育与儒学的关系。
《共和国教科书》出版的年代正是中国旧传统接近于破碎之时。所谓“接近于破碎”,一方面如1894年前后有士人观察到的“自今设再鼎革,非惟制义必废,即儒术亦将废”,但另一方面此士人认为“虽废,亦不能尽废,当如今之佛教为一线之延而已”。因此,《共和国教科书》之内容虽和儒学之大本大原格格不入,但有些课文在不经意中仍表现出一些儒术虽废,但亦未“尽废”的痕迹。

如《共和国教科书》中《孔子》一课会强调“本课言孔教之有体有用,不若宗教家之藉一神多神以惑人,故足为万世师表”。有时大概为迎合时势,《共和国教科书》也曾直接引北京政府之敕令入课文,以稍为孔子正名。如1914年在《教育公报》上发表的教育部敕令就曾被略作修改后收入《共和国教科书》,“教育部以孔子之道最切于伦常日用,为本国人所敬仰。其言行多散见于群经,故明定教育宗旨,通饬中小学校于修身、国文课程中,采取经训一以孔子之言为旨归”。
《共和国教科书》中会出现这些内容缘于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兴起,废止读经的过程并非如目前研究所描述的那样简单。以往多将废止读经的发端归于1911年革命功成和蔡元培的雷厉风行,这大致是个迷思。汤化龙就追忆说:
夫学校读经、讲经,自前清迄今,聚讼呶呶,考其沿革,约分四期。其始也以《孝经》、“四书”、《礼记》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以《诗》《书》《易》及《仪礼》为高等小学必读之经。既而知其卷帙繁多,理解高深,未足为教,遂改订章程,减少经本。前宣统三年,中央教育会议已经以经学义旨渊微,非学龄儿童所能领会,决议采取经训为修身科之格言,小学校内不另设读经一科,民国仍之。
汤化龙作为清末民初诡谲风云的亲历者,深知中小学废止读经一事所经历的曲折与繁复。其所分的四个时期大致以1904年《奏定学务纲要》颁布,1909年《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折》出台,1911年中央教育会会议召开和民国建立为界限,确为汤氏即时的所见和所感。在这一个“经书”不断少读,渐至于不读的过程中实际上充满着新旧之间的紧张、权势争夺的激烈与前后拉锯的反复。
从清廷主导全国教育的学部来看,1904年《奏定学务纲要》的颁布,已明确规定学堂不读全经。
中小学堂,科学较繁,晷刻有限。若概令全读“十三经”,则精力、日力断断不给,必致读而不能记,记而不能解,有何益处?且泛滥无实,亦非治经家法。兹为择切要各经,分配中小学堂内。若卷帙繁重之《礼记》、《周礼》,则止选通儒节本,《仪礼》则止选读最要一篇。自初等小学堂第一年,日读约四十字起,至中学堂日读约二百字为止。大率小学堂,每日以一点钟读经,以一点钟挑背浅解,共合为两点钟。计每星期治经十二点钟。中学堂每星期以六点钟读经,以三点钟挑背讲解……计每日读经一点钟,间日挑背讲解一点钟,每星期治经九点钟。至温经一项,小学、中学皆每日半点钟,归入自习时督课,不占讲堂时刻。
到1909年,不过五年时间,情况又发生了重大变化。5月学部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建议:
从前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分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历史、地理、格致、算术、体操八科,民间往往以科目过多,师资难得,经费难筹,坐是因循疑沮,有误时机。小学教育未能普及之故,此其一端。现拟酌量省并,约为五科:曰修身,曰读经、讲经,曰中国文学……惟原定各经卷帙较多,未便一律责以成诵。因《学》、《庸》理解高深,《孟子》篇幅太长,恐其记忆较难,现拟专授《孝经》、《论语》及《礼记节本》三经,缓授《学》、《庸》、《孟子》,将来并入高等小学堂教之。盖多读而不成诵,不如少读而成诵,于诵习经训较有实际。其国文一科,原定授课时刻每星期四小时,不敷教授,现拟将国文一科钟点格外加多,较旧章约增数倍,当不致有荒经、蔑古,道丧、文敝之虑。
此折得到清廷批准,付诸实施。当年10月张之洞去世,他曾是不读全经、立停科举之推手,但此时又是力图维持中学,开设存古学堂之巨擘。因此马上有人将张的亡故与经学式微联系在一起,说:“文襄逝后,国粹主义大衰。”又进一步指出,“纲常亦国粹之一,十年内恐将凘灭矣。京师诸耆宿之守死善道者亦不过三数人,其余则皆泰东、泰西之门徒。时变之来不可臆测,论者每谓中国进步迟,孰知学风波靡,捷于转蓬,南皮朝死,而存古学堂夕撤矣”。这些话恐怕都是在针对《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折》所说,特别是对此折中“经学”内容减而再减,且将以“国文”科取代“读经讲经”科的有感而发。
其实张之洞即使不死,学部对于中小学减少读经的大方向亦不会有多少改变,大概只会稍缓而已。这是因为调整“经学”在新学制内的位置一方面与学部中人的派系与新旧有关联,但更多是由学堂制度建立、学术分科后的大时势所推动。这个大时势推动着那些和新教育、教科书密切相关的东南新人物如张元济、黄炎培、庄俞、沈颐、蒋维乔等人不断发声来对中小学读经质疑和提出异议。
1902年张元济在《教育世界》上已撰文提出“勿滥读四书五经”,因为“往圣大义微言,髫龄之子,讵能解悟?强令诵习,徒耗丧脑力而已。天下事惟求其是,断非可以意气争。四书五经虽先圣遗训,而不宜于蒙养。至于今日,要已大明,则又何必故为袒护乎?愚意《论》、《孟》二书只宜中学。其它诸经必列专门,非普通毕业者,不令讲授”。
1903年张元济在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作序时又说,他在童稚之年读的是“十三经”,练习的是“八股试帖”,因此到十三四岁时“心界、眼界无一非三代以上景象,视世间事相去不知几千万里”。后来偶得《纲鉴易知录》方略知朝代更替,又读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二十四史,“顾皆卷帙繁重,不能卒读”。其缘故虽可能是自己“姿禀浅薄”,但更重要的大概是“其书之宜于浏览而不宜于教科”;现在《钦定学堂章程》出台,更清楚显现“以上诸书之不宜于教科矣”。因此商务编撰的新式教科书令张氏感到“吾方恨少时无书可读”,生于今日者“宜自幸而发愤致力于是书”。可见教科书出版与经书的教授从一开始就已明显呈现互不相容的态势。
到1904年《时报》上有人评论《奏定小学堂章程》,提出要“毅然删去讲经读经一科,将经籍要义归并诸修身科中”。此文虽然未明确撰者,但从《时报》的编辑、作者群推演之背后清晰可见的是当时已出现的一个以上海为中心,以江浙为基地的新人物所联结而成的权力网络。这一权力网络以《时报》、商务印书馆、江苏省教育会、预备立宪公会等出版机构、社团、学会为运作空间,其势力从清末一直延续至民国,经久不衰,日趋膨胀。
此网络中人最着力事之一是编写、推销中小学教科书,而要推销中小学教科书,各学校若仍然读经大概就要平生不少阻碍。由此,蒋维乔、顾实等屡屡在《教育杂志》和《东方杂志》上发表激烈文字来攻击读经。前述小学堂章程不断变更,诸“圣经”的阅读量大减,很大程度上正是上海这个趋新网络不断发文攻击,造滔滔舆论的成果。
小学堂章程每星期教授时刻表:高等三十六小时,初等三十小时,读经、讲经各占十二;夫于三十小时之中,使读经、讲经占其十二者,其要义将使圣贤正理深入儿童之心,以是端蒙养之本,所期望于国民者至厚。顾保存国粹,诚不宜荒经而蔑古;而古人浅近之语言,自今人讲习之,无一非深邃之文义,童年索解尤苦其难,故小学教员惟此科成绩较少。在高等小学之生徒,国文程度较深,聪俊者或亦领会过半;而初等小学中虽有聪俊之生徒,尚不过什解二三;此外则成诵已颇艰涩,中材以下往往敷衍终课,随班而退。教员之经验较深,及生徒家族之知识较优、责望较切者,谓不如多习国文、算术,可为生计之预备,是诚至言。
至1911年,庄俞、何劲、黄炎培等人的态度表现得更为决绝。庄氏在《教育杂志》上直接撰文追问:“所异者,必强列读经讲经一科,不知何解。”黄炎培则在视察昆山官立高等小学的报告中指出,教员虽然讲经“极清晰”,但他却越发感到“全讲经文断非小学教科所宜”!
至同年夏天北京召开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议(即中央教育会会议),这些主张“废经”的人物之意见开始从滔滔舆论进入付诸实施层面。他们先着手的是提议初等小学废读经讲经课。当日此提案“争议甚烈”的情形在《申报》上有非常详细的现场纪实报道:
小学不设读经讲经课一案,胡家祺登台说明小学不能不废止此课之理由。吴季昌登台演说,大约反对停止小学读经讲经。程澍海登台演说读经讲经宜用节本,由学部编定。俾聪颖可以参考全书,鲁钝者领略节本。林传甲登台演说此项功课万不可废,历叙日本、俄国、西洋均研究中国经书。中国竟废去,是废经畔孔,是丧失国粹,语涉题外,经各会员请简单发言,林犹大声急呼,痛哭流涕,击案顿足,经一句钟之久。众叱责之,林犹不止,会场秩序大乱。某会员谓时已十句三十分,请宣告休息,会长宣告休息。众退出会场,林始下台。
十一句钟,复入场。会长谓适间秩序大乱,未免可惜,会场言论本属自由,但望诸君于范围内讨论真理,嘱办事官宣读会议规则第十二、三、四条,请众遵守。黄炎培登台演说小学之读经解经不能不废,从教育上研究及保存国粹上研究,有此功课均属无益。贾丰臻登台演说外国无经学,不能以外国章程论。但就《大学》朱子序文论之,由小学以至大学皆有层次,亦未言小学即须读经讲经。有明以来注重科举,始以读经讲经为主要,请众研究。
马晋义登台演说侯会员此案并非废经,不过因儿童之心理,读讲无用,故议停止,但就社会上心理言之,遽然废止恐于学务上有碍。现学部已改章,初等小学自第三年起始读经,似于实际上颇有斟酌,众可研究。陈宝泉登台演说与马晋义所言略同,改在第三年读讲尚可实行。姚汉章登台演说各会员有看此案太重者,有看此案太轻者,本员以为此案当从教科支配上研究。
时场中欲发言者甚多,会长谓已有赞成反对即作为讨论终局,嘱办事官宣读胡家祺等提议初等小学不设读经、讲经课,节录经训定为修身科之格言案,并宣告此案重大,用无记名投票法表决,可者用白票,否则用蓝票,先由办事官分票后,由办事官收票,共会员百三十五人得白票八十一,蓝票五十四,遂表决。
以上是中央教育会第14次会议的情形,“废经”一方大胜。张元济、黄炎培等本欲乘胜追击,让中学和高等小学也取消读经讲经科,但没想到第16次会议讨论时,孙雄(即孙师郑)当场“宣读景庙时圣训(关于读经讲经者)二道,感动人心,中学及高小读经课程遂得保存”。
数月以后,国体入共和,但这并不意味着各方争论中小学校读经事的结束。对于趋新人士,尤其是与商务印书馆有关联的诸人而言,此事除了涉及思想的新旧之争外,还关乎教科书的生意。于是1915年北京政府颁布的《特定教育纲要》就被他们认定是开复古的“倒车”和读经的回潮。
其实平心观之,当时北京政府对于中小学读经的“回归”程度相当有限。不过是初等小学在第三、四学年授《孟子》,高等小学第一学年起读《论语》,且明确规定,“各校不得借口读经,锐减各科教授时刻”。读经时刻的多少以小学毕业时读完《论语》、《孟子》两书为准。中学校则是从《礼记》中节读《大学》、《中庸》、《儒行》、《礼运》、《檀弓》等篇,《左氏春秋》同样也是节读。
关于这个读经的量的大小,我们可以参考几位和袁氏复辟压根无关系的读书人的意见。1913年末,杨昌济提出“民国之废读经,自有其教育上之理由”,在于“书经、易经,多古奥难解,不适于为教授之材料”,所以希望能由“明习经术之士,取经说之极精要者,编入国文教科书及修身教科书中”。这不正是“中小学校于修身、国文课程中,采取经训一以孔子之言为旨归”?
但杨氏的讨论并未停留于此,他进一步说:“若必欲以读经示尊孔之义,则专读《论语》或尚可行,因篇章不多,文义浅显,尚不致过重儿童之负担”;又说:“其他各经可参择教授者甚多,如《诗经》之诗,有可选入国文读本者,《礼记》中之言礼意者,可作中国伦理教授之材料”;“《左传》、《公羊传》、《孟子》,皆吾国第一等好文字。《史记》亦宜选读”。他特别指出:“时人所作之文字,反不如《孟子》、《史记》之易解。余尝亲试之矣。以前清时文字,教余之子女,彼等苦其难解,及教以《公羊传》及《史记》,则彼等甚喜读之,故施教之序不可紊也”。
汪康年之弟汪诒年则指出:“《孝经》、《论语》、《孟子》及《诗经》之前半部,实不可以不读,卷帙无多,并不多占时间,又大率理深而语浅,但使教习善于讲解,学生亦不难领会。”
可见袁政府所定的“经”的阅读量相较于清末学校读经所规定的量只少不多,对比一般读书人关于读经量的认知也近似。即使这样,由于经过了清末到民初极其激烈的新旧之争,且这种新旧之争并不只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深深牵涉到了实际利益层面,因此趋新一方只要见到“读经”二字就全力以赴攻击之,以将其塑造成为一种天然的政治不正确。
更诡谲的是,北京政府的读经“回归”又因其“有限”而受到了孔教会一系的激烈反对。这是因为当时北京政府的立场大致是要调和两面:一面要“救经学设科之偏”;另一面则希望“不蹈以孔为教之隘”。教育总长汤化龙就提出:
兹二说者(按,读全经与立孔教),似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不免得其偏而遗其全……经书固宜课读,然一经之中,深浅互见;设非节取为教,强以难知,贻误学童,良非浅鲜。孔子为人伦师表,历代均致尊崇。顾必谓推孔子为教主而道始尊;微论孔圣未可附会宗教之说以相比伦,而按之国情及泰西宗教之历史,均难强为移植,致失孔道之真,而启教争之渐。
因此教育部在要求以孔子之言为旨归时会特别说明:“其中不可不辨者,一则尊孔与国教不能并为一谈;一则读经与尊孔不能牵为一事。以立教为尊孔,于史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也。以读经为尊孔,经籍浩繁,义旨渊博,儿童脑力有限,与其全经课读,诸多扦格之虞。”
汤氏的这些意见被新人物看作落伍守旧,而在孔教会中则被看作“祸心暗藏”,他们激烈指责汤氏意见道:
托崇经尊孔之名,行毁孔蔑经之实者,其居心尤险毒,取术尤巧诈。其事若行,则诬孔而人不知,亡经而人不觉,中国之精神命脉从此斩焉而绝,无复生之望,此真邃古未有之变,普天不共之仇……其事维何?即教育部呈大总统宣明教育宗旨之文……庶以救经学设科之偏,复不蹈以孔为教之隘等语。果如所论,则孔子不得为圣人,六经不得为圣经。教育部之智识高出于孔子万万,教育部所编之教科书,高出于六经万万,然后可也。明明割裂圣经,而曰吾以救经学设科之偏,且曰是崇经也,是采生折割人者为爱人也。明明谓孔子之言为未足,而曰吾不蹈以孔为教之隘,且曰是尊孔也,是毁人者为敬人也。不意绾教育之大权者,其狂悖乃至于是。推其故不过藉此以悦庸众,固权利耳。为固一己之权利,而不惜断丧一国之元气,干犯举世之清议,亵侮至尊之先圣,贼害将复之人心,盖其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亡已久矣。亡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者非人也。以非人者而当教育之任,几何不胥天下之人而不如禽兽也。
北京政府的读经“回归”遭到两面夹攻,说明如何看孔子、如何对儒学、如何读经、如何立孔教等在民初读书人心中有纷繁多重的意义和层层叠叠的纠葛。1913年杨昌济就指出,“孔子但说现世,故不得以儒术为宗教”,不过“若为广义的解释,则孔子受全国人之崇拜已二千余年,实亦具教主之资格。吾人既设庙祀之,即不能不认孔子为有半神之资格”。
这番话的曲折实揭示了民初各方的心目中有多重孔子在焉:有欲立孔子为教主以重振世风国运者;有将孔孟之道抽离其立说之根基,而试图将其客体化、对象化者;亦有想借儒家学说救人心、社会之弊者。情形可谓异常复杂。
这种复杂情形在《共和国教科书》和其他各种教科书中都会有所反映。如孙毓修编写的《新说书》同样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其通篇均是关于地球大势、美国革命和中国国耻的时髦新知,但同时也会赫然出现“至圣孔子像”和“亚圣孟子像”的广告。这是因为进入共和后,读经虽然废止,但各学校拜孔子之典礼依然按时举行。蔡元培在回应林纾的批评时亦特别强调除了君臣一伦已不适用于民国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
此外,民初教育对于现代国家和世界的理解也有颇值得讨论之处。以《共和国教科书》为例,其编写者大多都曾是从小束发读书的士人。他们的观念世界多受到源远流长的“天下”观念和晚清流行的“公羊学”之影响,因此其思考范围就不太会局限于单一国家。由此,《共和国教科书》中时常会有超越民族国家和机械进化的内容。这一点和清末特别强调民族国家的情形已不太一样。
1906年《钦定教育宗旨》把“尚武”、“尚实”等理念作为教育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蔡元培在民初反驳说:“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也”,但是“强兵富国之主义。顾兵可强也,然或溢而为私斗,为侵略,则奈何?国可富也,然或不免知欺愚,强欺弱,而演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则奈何?”对此,蔡元培给出的方案是“教之以公民道德”,辅之以美育和世界观的教育。何谓公民道德?蔡氏一面指的是泰西尤其是法国革命中所说的自由、平等、博爱(原文为亲爱——笔者注)等要素;另一面也包括中国经典中的义、恕、仁等核心价值。
两者的结合使得《共和国教科书》对何谓自由、平等、共和之精神等均有专篇讨论,这是一种新的有关citizen的价值观的输入与养成,但同时又为新的价值观羼入中国传统元素。对此已有许多研究者有过讨论,兹不赘述。
同时两者的结合又使得《共和国教科书》有了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世界意识和人类意识的内容。如它讲义和团会特别区分爱国心和排外心,又强调“排外与爱国心截然不同”,“盖排外者出自偏激之感情,亦即利己心之变相。其意若曰不排挤之,足损我私利也。故排外之情倏起倏灭,今日排外而明日媚外者不足异。何则?其心目中本但知有一己利害也,若爱国者不然,彼挟其明晰之理性,坚定之意志,而为远大之计划,故不惜牺牲身家之利害,以殉国家”。进而《共和国教科书》会从“人爱其类”的理由出发阐明“对待外国人之道”。在《世界强国》一课的教授法中编者就着重指出:
所谓强国,非仅地广人众之谓,亦非仅军备充足之谓,要必人民有进取之精神,国家有完善之制度。若学问、若实业及其余各端,俱有蒸蒸日上之势。原因甚多,非旦夕所致也。
正因对何谓“强国”有这样的理解,《共和国教科书》在小学生毕业前夕才会通过课文要求学生学会做“大国民”。所谓“大国民”,“非在领土之广大也,非在人数之众多也,非在服食居处之豪侈也”,而是要“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
《共和国教科书》强调“大国民”要“无不各尽其道”,说明此时对清末过度强调“富国强兵”的反思已经露出端倪,五四时“一般青年学子憧憬于一种大同世界的幻影”,正和民初教育的转型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也说明中国古老的“道不远人”之教育理想在民初仍有其余绪。钱基博就指出:“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这种“循其性之自然”的教育之道并未隐退,反在时人议论中时有显现。像章太炎就以为:
自新教育潮流输入,亦复守其故说,纳一切学术于书本。师以是教,弟以是率,而不知教育之为道,正不尔尔。盖教育家,非能教人育人,在能使人自教育而已,彼以书本为教育,实属大谬。教育事业,精神事业也。譬之于礼,鞠躬长揖,端跽下拜,彼人自行礼,而教育家从旁赞之而已,曾何力之有焉?
阎锡山在1921年召开的“进山会议”上曾专门召集其麾下幕僚来讨论什么是“道的教育”。在阎氏看来:
道的根本,非在身外。人受中生,又生而有欲。中者人之所以为贵也;欲者人之所以资生也。道的教育在使人保其中而不然乎习,养其欲而能顺乎理。明白的说,己所不欲,不施于人,是道。教人己所不欲,不施于人,即是道的教育。
这些对教育之道的强调源自于《易经》“蒙卦”中所说的“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与《礼记》“学记”中所谓,“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往后则可以延伸到1940年代,潘光旦仍然在说:“好的教育正是要使青年多多的自动”,教育的过程要努力“激发与激励此种自动的力量”。
民初虽然不少读书人和政治家仍然不乏“道不远人”的教育理念,但总体而言他们并不能抵抗现代潮流席卷而来后“天下为学说裂”的时势。这一时势造成了科举废除、圣经弃读和书院消亡,留下的尚有私塾、家学和一些卫道的人物。这些仍有可能载道的空间与人物虽然在地方社会一直具备相当的权势,但新学对于旧学之“凌驾”是更为凶猛的潮流。这潮流拍岸的结果或可看作趋新启蒙对于守旧复古的重大“胜利”,但若仔细审察其演进的历史过程,即使其能够被称为“胜利”,但在这个过程里仍包含许多由“胜利”带来的不堪言与不忍言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新”教育的推行貌似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但其如何去做却总是处于不断地“调整”和“尝试”的“未定”状态之中,而在这一过程中被消耗和伤害的是万千青年的具体运命。1937年张元济就感慨道:“近几十年来,设学堂、讲究新学……国家受了不少的益处,但是在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佚、贪污、诈伪、鄙贱、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使我国家糟到这样的田地,不能不说也是它的结果。回想四十年前,我们在那里提倡新教育的主张,到今朝,良心上也受着狠严重的谴责。”而对于这种消耗和伤害潘光旦有过更具体的阐发。他说:
近代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和国家的地方。……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
近代中国的教育没有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公民、平民,或义务教育,二是职业或技能教育,三是专家或人才教育。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第一种目的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说得最好听,也无非教人取得相当的所谓“社会化”至于在“社会化”以前或“社会化”之际,个人应该有些什么修养上的准备,便在不论不议之列。第二种教育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专教人学些吃饭本领,绳以“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原则,这种教育原是无可厚非的。但至少那一点“荣辱”的道理应当和吃饭的智能同时灌输到受教育的脑筋里去,否则,在生产薄弱,物力凋敝的今日,也无非是教“不夺不餍”的风气变本加厉而已。第三种所谓人才教育最耸人听闻,其实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专家教育以至于文官教育,和做人、做士的目的全不相干,弄得不好,造成的人才也许连专家都当不了,文官都考不上。
另一方面近代中国“新”教育未立,行之千年的传统教育虽然并未完全倾倒,但在思想和舆论层面已被趋新读书人彻底地“污名化”。光绪年间一本教蒙童识字的书就直指“村学究之书塾俨然一囹圄”。1909年出版的《图画日报》在谈到私塾时认为,“其所谓蒙师者类系粗识之无,毫无程度之人。以故塾中弟子之功课一切殊不可问”,因此“若辈应在天然淘汰之例”。包天笑在1912年所写的一本《共和国宣讲书新社会》里也大谈特谈了一番入学堂的好处与进私塾的可怕。1916年考过科举且做过塾师的师范教习张棡作教育新剧,也是要写“科举时代教育腐败,一老秀才聚徒讲学,适丁科举之废,新学朋兴,而老生不服调查,大起冲突”。以上或都可看出在新教育跌宕推行和传统教育急剧失势的合力催逼下,中国读书人群体的分裂与学问的分裂。
在此种情况下中国的读书人虽然从教科书中获取了不少舶来新知,却很难在教科书里找到为人立身治家处世的大义,而陷入无穷的困惑之中。因此民初教育转型背后的核心问题或正在“道不远人”的理想与“天下为学说裂”的时势间的牵连与纠葛。民初教育结构、理念、内容的多重矛盾面相让当时的读书人无所适从。面对席卷而来、咄咄逼人的新潮,他们既不愿选择随波逐流,亦无法待在原地,颟顸强守。正是在如此纠结与无奈的历史条件下,民初教育在“变亦变,不变亦变”中艰难前行,直到教育之“道”与天下之“道”彻底被形形色色的外来“主义”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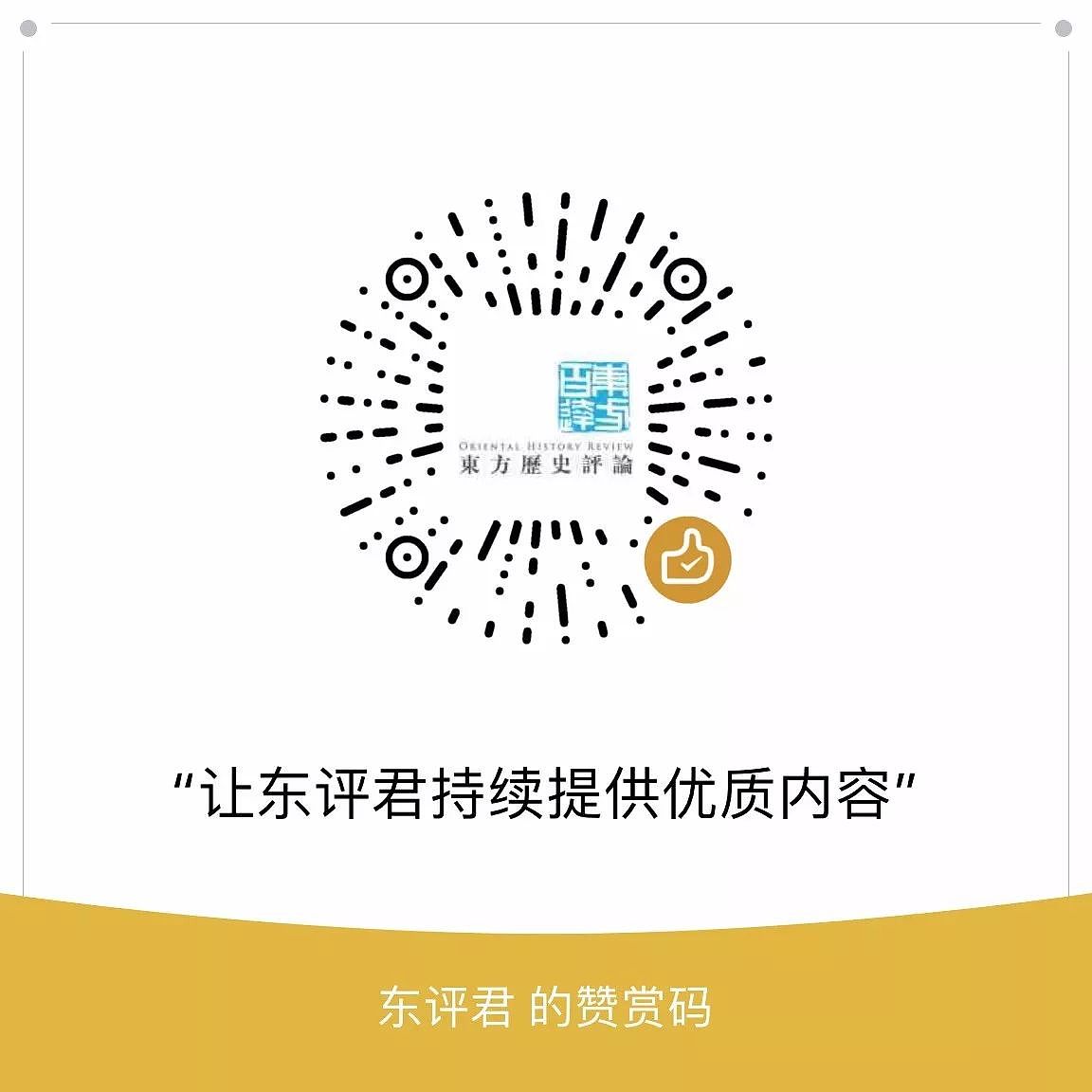
点击下方蓝色文字查看往期精选内容
人物|李鸿章|鲁迅|胡适|汪精卫|俾斯麦|列宁|胡志明|昂山素季|裕仁天皇|维特根斯坦|希拉里|特朗普|性学大师|时间|1215|1894|1915|1968|1979|1991|4338|地点|北京曾是水乡|滇缅公路|莫高窟|香港|缅甸|苏联|土耳其|熊本城|事件|走出帝制|革命|一战|北伐战争|南京大屠杀|整风|朝鲜战争|反右|纳粹反腐|影像|朝鲜|古巴|苏联航天海报|首钢消失|新疆足球少年|你不认识的汉字|学人|余英时|高华|秦晖|黄仁宇|王汎森|严耕望|罗志田|赵鼎新|高全喜|史景迁|安德森|拉纳・米特|福山|哈耶克|尼尔・弗格森|巴巴拉・塔奇曼|榜单|2015年度历史书|2014年度历史书|2015最受欢迎文章|2016年最受欢迎文章







 +61
+61 +86
+86 +886
+886 +852
+852 +853
+853 +64
+64


